版權聲明:本文版權歸文章作者所有,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不用於商業用途,僅為學習交流之用,如文中的內容、圖片、音頻、視頻等如有侵權,請及時聯系本站站長刪除。
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知識產權家】
孫遠钊
美國亞太法學院研究院執行長
暨南大學特聘教授
本刊專欄作家
“中國知網”(簡稱“知網”)近來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在展開相關討論之前,約25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幾起事件,或許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反思的教訓。
一場內容數字化的鏖戰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類正式進入了互聯網和電子商務時代。作為最具指標性的新聞報業單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高管層已然認識到,未來將是以數據化的新聞和評論出版為主的市場。於是,《紐約時報》與兩個頗具知名度的數據庫廠家(如“律商聯訊”NexisLexis®等)簽約,將該報曆史上的所有內容全部數字化,並提供線上檢索服務(需要付費,且費用不低),也制作成光盤出售。這些數字化內容包括了由27000餘名自由作家(freelancers,不是《紐約時報》的正式雇員)撰寫的文章。《紐約時報》在上述協商、訂約的過程之中,從來沒有同這些作家或其隸屬的作家協會(工會)打過任何招呼,從付費檢索服務獲得的收益,也自然悉數進了報社的口袋。
自由作家們當初通過作家協會的集體協商與《紐約時報》簽約時,完全是以傳統實體的紙本報紙為基礎,根本未曾觸及內容數字化與相關的電子檔案的處理問題。眼看報社又開辟了新的收益渠道,卻把他們全給晾在一邊,自然十分不快。於是,全國作家工會(National Writers Union)的時任會長喬納森·塔西尼(Jonathan B. Y. Tasini,下圖)牽頭,聯合其他5名作家共同起訴《紐約時報》和另外5家媒體與數據庫公司,主張其未經許可擅自使用了他們從1990年到1993年之間撰寫的文稿,構成著作侵權。被告則抗辯,報紙一經刊登,就構成了對原來個別作品的改編(revision),並組合成為了一個演繹或派生的匯編作品(collective works),出版者也就享有匯編著作權,因此自然可以自由地從事對其中內容的處置,不需要再經過原作者的同意。該案件在初審時原告敗訴[主審法官是後來成為聯邦最高法院有史以來首位拉丁裔女性大法官的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M. Sotomayor)],但之後,上訴法院推翻了初審判決,繼而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再審。全案的爭議焦點是:“匯編著作權”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它的範圍及於何處?該權利與各個單篇文章原作者的著作權的關系如何?

Jonathan B. Y. Tasini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上訴法院的認定,判決共同被告《紐約時報》等構成侵權。在解釋美國《著作權法》相關條款的含義時,法院表示,被告出版商無法用匯編著作權來覆蓋其整個數據庫當中的所有作品,因為根據使用者的檢索要求,數據庫從事了對個別單篇作品(而不是連同整個上下文)的複制和發行。由於被告把數據庫比作“電子圖書館”,法院也就借此指出,當使用者想要檢索某篇文章時,數據庫提供的並不是含有該文章的整份報紙或特定的期刊,而是直接抽取並複制、發行了特定的單篇文章,這就完全超越了其本身匯編著作權的範圍。換句話說,通過該判決,法院明確了匯編著作權的範圍僅及於有匯編者貢獻的獨創表達部份,包括最終呈現的篩選、編排、組織與排列,別無其他。
經過8年艱苦的司法鏖戰,這一判決猶如宣告了“大衛戰勝歌利亞”式的奇跡。然而,就在自由作家們還來不及慶祝時,《紐約時報》就祭出了殺手锏:其準備把和本案相關的,之前與《紐約時報》沒有訂立許可合同的27000餘名作家從1980年到1995年的115000多篇文章悉數從其數據庫中刪除。按該報時任發行人兼董事會主席小阿瑟·奧克斯·蘇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下圖)的表述,《紐約時報》“現在要采取艱困且傷感的程序,從曆史性的電子文檔中把相當一部份移除”。其他的一些出版商,如《時代雜志》(Time Magazine)等為了避免法律風險,也紛紛跟進,準備采取類似的行動。

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這些後續發展幾乎都被撰寫本案反對意見的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大法官(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完全預料到了。他在意見書裡表示,“鑒於尋覓個別自由作家的困難與遭到法定賠償的潛在風險,很可能會產生強迫電子文檔系統從數據庫中清除自由作家作品的後果。”他還預料多數意見的判決不會帶給自由作家們任何額外的實質性財務收益。他在反對意見書中摘錄了由著名制片人肯·伯恩斯(Kenneth L. Burns)具名提呈的“法院之友”書狀(amicus curiae brief)當中的一段文句:“從電子典藏中刪除這些材料,無論是基於任何理由抑或僅是一個偶發的原因,大規模的刪除都將破壞電子檔案對曆史研究者所能提供的最主要效益——功效性、正確性和完整性。”
雖然主筆多數意見判決書的露絲·貝德爾·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J. Ruth Bader Ginsburg)也意識到了判決可能會產生的後遺症,她依然認為必須在法言法,況且,這樣的極端結果未必真會發生;即使真有窒礙難行的問題,各方當事人或可通過談判協商達成某種妥善安排;國會也可考慮通過立法,對這類作品的許可、複制、發行和相關費用的配置等事宜給出必要的指引。
《紐約時報》方面也不是埋頭硬幹。他們自是十分明白,無論該案爭議最終如何解決,將來報紙的許多版面還是必須依賴這些自由作家的稿件來填充。因此,沒有必要在輸掉了官司之後還要繼續作絕,以避免在社會上留下惡劣的形象,破壞自身長期積累的名聲。所以,在正式動手刪除檔案前,《紐約時報》給自由作家們開設了一個專門的網站和電話熱線,只要自由作家們自願同意簽署一項協議,給予《紐約時報》全球範圍的非獨占許可,就可以避免作品遭到刪除的命運(這也意味著《紐約時報》無須再行支付任何額外的許可費)。最終,約有20%的自由作家選擇接受了這一條件。至於《時代雜志》完全沒有采取類似的做法,就直接從數據庫當中刪除了可能構成侵權的文檔。
《紐約時報》的上述做法,無疑是綿裡藏針的高招,同時兼顧了面子和裡子。明明是敗訴方,卻以刪除檔案為籌碼和杠杆,不聲不響地化被動為主動,反而讓獲得勝訴的一方幾乎完全陷於被動。至於塔西尼本人和其他不願屈從的自由作家們,則從2001年9月10日開始便在《紐約時報》總部前打算進行長期性的抗議活動,並準備呼籲罷工,威脅讓報紙的多個版面“開天窗”。不料,第二天上午,紐約市就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於是塔西尼等人的計劃不得不順延到翌年1月2日,但已勢成強弩之末。《紐約時報》雖然曾與這些“鷹派”作家們進行過象征性的協商,但整個協商進程極度遲緩,自由作家只能選擇接受報社開出的條款,或坐視自己之前貢獻過的文章從電子數據庫當中完全清除。
本案中,6位自由作家在訴訟中贏得了一場重要的“戰役”,獲得了象征性的勝利,但卻因此讓自己和後來的自由作家們輸掉了整個“戰爭”,情況反而比起訴之前變得更差了。現在,任何想向《紐約時報》投稿的自由作家,從一開始就必須簽署一份“職務創作協議”,從而完全失去了在合同期間內對自己未來作品的控制權,自然也就失去了更多的獲得收益的渠道,因為他們將不再能把自己的作品分享給其他的媒體同時或後續刊登。《紐約時報》則是最大的贏家:其不僅不需要支付任何正式職員的常態性薪資與社保、退休金等額外支出,還獲得了完全等同的文稿貢獻,甚至是獨家報道或評論,更可從電子檢索中獲得額外的收益,而無須分享給原作者。塔西尼後來也因此和其他一些原因而黯然下臺。後來,塔西尼成為民主黨的選舉顧問,並兩度協助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參議員競選總統。
但是,該案中真正的最大輸家,恐怕是著作權法制和社會公益。法院依法論法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其給出的法理說明也無懈可擊。但是這樣的推導卻正好產生了著作權保護體系制定之時最不樂見的結果,不但再次顯示了法律的局限性,也讓本來寓含重要公益意義的數據庫價值受到了相當的減損,更與著作權法保護文化資產與創意的本意背道而馳。
不過,就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出臺後不久,受到該判決的鼓舞,作家協會(Authors Guild)、美國新聞從業人員與作者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Journalists and Authors)、全國作家工會等聯合超過3000名自由作家,共同起訴了《紐約時報》、道瓊公司(Dow Jones,《華爾街日報》的所有者)、湯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奈特·裡德報業集團(Knight Ridder)、裡德·愛思唯爾出版公司(Reed Elsevier PLC)等主要媒體和數據庫提供者對60萬篇作品構成侵權。這場集體訴訟的真正目的,無非是給出版方加大壓力以促使達成和解。然而,雙方的談判一共拖延了17年,最終於2018年4月達成了協議,由出版方一次性賠付9400萬美元,並負擔律師費及其他費用。由於每位作家的情況並不相同,其中一些人從未申請版權注冊,所以,最後分配到每位作家的賠償金額的計算過程極為複雜,不同作家獲得的賠償金額彼此也有很大的差異。
另一場鏖戰與“載體中立”法則
同樣受到“塔西尼案”的影響,18位曾經在《國家地理雜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刊載作品的自由作家和攝影師聯袂起訴該雜志的主辦者國家地理學會和尹士曼·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起因是被告計劃將該雜志自1888年創刊號開始的所有內容數字化,並制作成光盤出售,即《國家地理完整版》(The Complete National Geographic)。顯然,該案中,被告事前也完全沒有知會獨立作家和攝影師們,更遑論支付額外的費用。
與“塔西尼案”不同,《國家地理完整版》采用電子掃描方式制作,用戶從屏幕上可以看到與該雜志原始紙本完全一樣的文字、圖像和內容,並按月紀年依序排列。換言之,光盤版對於原始版本的內容、編排、格式或表現等都沒有做出任何改變。
審理本案的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表示,雖然被告在新的匯編作品(光盤)當中增加了一些實用性的功能,但只要這些附加的事物或功能沒有在本質上改變原始匯編作品(紙本雜志)的完整性,便還在著作權法“容許改編”(permissible revision)的範圍之內,符合“載體中立”(media neutrality)的要求。法院因此判定,《國家地理完整版》沒有對自由作家和攝影師的原始作品構成侵權。
由於“塔西尼案”和該案的判決,“載體中立”已成為出版商保全和行使其匯編著作權的重要原則。將書面(紙本)轉換為電子格式時,如未對其中的各個原始作品造成任何本質性的變更,則出版商可以主張適用“容許改編”來運用其本身的匯編著作權。無論如何,將一個版面中的個別作品單獨抽取使用,都會被法院視為構成了本質性的改變;該行為如果未經事前許可,便構成侵權行為。
知網引發的問題
知網近年來在知識產權方面引發的問題主要有四:
其一,知網所收錄的大量期刊文獻,其中究竟涉及哪些權利,歸屬於誰?
其二,如果知網不擁有著作權,其是否取得了合法許可?抑或構成合理使用?
其三,知網提供的文獻查重功能不對個人開放,是否構成濫用壟斷地位?
其四,知網案件的損害賠償與後續整改措施應如何確定?這對知網的長遠發展有何影響?
著作權存在與否及其歸屬
有調研顯示,自2004年同方知網(北京)數字出版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以來,由該公司擁有和運營的“中國知網”與其分身《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以下統稱“知網”)已先後經曆超過1500起訴訟,其中至少有1100多起涉及著作權歸屬或侵害原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知網提出的主要抗辯包括:(1)其已經取得了期刊的許可(“獨家授權”),將曆來在期刊上刊載過的文獻悉數匯編收錄到自身數據庫和相關產品之中,並“通過光盤、網絡、手機登載體進行出版發行,提供信息服務”;(2)其享有對期刊的匯編著作權;(3)縱使其權利不及於各個單篇的原始作品,其數據庫或電子期刊仍可適用報刊轉載法定許可的規定,不經作者許可而從事使用(即合理使用)等。值得注意的是,據“知網”自身的表述,其數據庫通常與學校或期刊合作,不與作者直接對接。換句話說,作者在向期刊投稿時,就應看到投稿須知中的“稿件將編入知網數據庫”等表述。
截至目前,不同的法院都沒有接受或支持上述抗辯,導致知網迭遭敗訴。不過,由於個案的損害賠償金額相對有限,所以頻繁敗訴對知網的整體運營收益幾乎沒有產生任何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一經判決敗訴,知網便會立即把涉案的相關電子文檔悉數從其數據庫中刪除,反而讓原作者的文獻無法呈現或被檢索到。由此可見,不分國界,也無分國情,知網的反應和行動與前述《紐約時報》《時代雜志》和律商聯訊數據庫等幾乎完全一致,但由於知網目前是中文學術文獻查閱領域使用範圍最廣的服務提供者,相關案件也就寓含了更大的公益因素,知網數據庫的質量、內容勢將對研發創新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國現行《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匯編若幹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構成作品的數據或者其他材料,對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體現獨創性的作品,為匯編作品,其著作權由匯編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這與域外或國際間的規定基本一致。再綜合梳理中國法院曆來對知網的論述和認定,至少可得到兩點結論:其一,知網將涉案文章收錄並提供下載服務,不屬於期刊與期刊之間的轉載或摘編行為,因此不適用《著作權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知網無法主張其構成“法定許可”;其二,每一期刊在文章的選擇、編排方面如體現出一定的獨創性,即構成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匯編作品,無論是否征得被匯編文章作者的許可,其著作權均由匯編者享有,匯編者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使用匯編作品,但其範圍不及於也不涵蓋各單篇文獻的原始著作權。換句話說,除非另有證據,知網對單篇文章並沒有任何著作權。
著作權的使用許可
《著作權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許可使用合同和轉讓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轉讓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對於知網或其轉載來源的期刊雜志社經常僅通過單方、制式性的聲明主張享有各單篇文獻原作者的著作權的做法,目前學界的觀點與法院的判決相當一致,即均認為無法僅據此便認定期刊已經取得了著作權或是有效的使用許可。
例如,在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趙德馨教授與知網的論文著作權糾紛案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定,刊載作者論文的期刊僅憑格式化、概括性的聲明或協議,在既沒有作者的簽字確認,原作者亦不認可該證據的情況下,不能證明原作者將涉案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轉讓給期刊雜志社,即無法認定刊載論文的期刊雜志社取得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其與知網簽訂數字出版合作協議書的行為屬於無權處分行為。知網向不特定公眾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載閱讀服務,侵害了原作者對涉案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在學界觀點方面,中國人民大學李琛教授對知網以單方聲明取得原作者著作權持非常保留的觀點:“綜合判斷作者有無許可信息網絡傳播權並允許期刊社轉授權的意思表示〔,〕如果無法明確作出這種推斷,應作有利於作者的解釋。……即使聲明的內容非常清晰,考慮到期刊社的聲明屬於格式條款,在當前的科研考核體制之下,作者處於弱勢,如果結合授權範圍、報酬數額等因素判斷聲明的條件明顯違反公平原則,要根據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條、第四百九十八條檢驗其是否無效或應作有利於作者的解釋,而不能當然地認可聲明的效力。”
中國政法大學劉文傑教授也認為:“著作權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本法規定可以不經許可的除外。除外情形主要是指著作權法中有關法定許可及合理使用的規定。雜志社的單方聲明存在如下問題:一是投稿作者可能並不知曉,二是聲明內容模糊寬泛。而根據著作權法第29條的規定,許可使用合同和轉讓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轉讓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實際上,著作權法不但要求就作品使用訂立許可合同,還要就許可事項作出明確具體的約定。雜志社的單方聲明很難滿足這些要求。換言之,雜志社若要從作者處取得信息網絡傳播的授權或者轉授權的權利,應當與作者訂立合同,同時,授權條款應當公平合理。”(按,劉教授在此顯然是把“授權”和“許可”兩個名稱交替使用。)
然而,知網在其網站上的“版權聲明”卻仍然從一開始便表示,“中國知網的全部內容均已獲得權利人的授權”,非常可疑。無論如何,知網案與前述的美國“塔西尼案”等固然在具體事實方面有所不同,但最終都涉及期刊與數據庫提供者無權處分匯編作品中個別單篇文獻作品的問題,知網案也產生了與“塔西尼案”同樣的困境:既然被告被判決構成著作侵權,那麼理應立即刪除或銷毀相關侵權;涉及電子檔案時,把相關侵權物從數據庫中移除,也屬天經地義,是維權執法的主要目標之一,無可厚非;然而,這樣的處置卻顯然與社會公益和著作權保護體系的立法宗旨產生了嚴重的沖突,導致了“滿盤皆輸”的不良後果,也讓知網陷入了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兩難困局。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是,如果知網如同前述的《國家地理雜志》案一般,將原紙本期刊的整體排版予以掃描、制作成電子檔案,並收錄到其數據庫,是否有可能因“媒體中立”法則而得以免除侵權責任?對此問題,目前尚無司法判決或解釋可為依循,但鑒於知網重大的公益性,這或許可作為知網未來整改的一個方向。
知網是否構成濫用壟斷地位
這個問題至少涉及以下兩個環節:
第一,知網采取被媒體稱為“借雞生蛋”的運營與盈利模式,即一邊通過期刊雜志出版單位直接收錄著作權人作品,另一邊在未明確獲得作者本人許可的情況下,在網絡上傳播、供使用者下載以獲利,而文獻作者卻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報酬,甚至連下載自己的作品都還需付費。在此,知網是否構成濫用壟斷地位?
第二,知網提供的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通稱“論文查重”服務)之前一直只提供給其指定的機構(非自然人會員)使用,未對個人用戶開放(2022年6月12日已經宣布開放,但仍須收費)。鑒於“查重”已經成為當前所有高校教師、學生等必須使用的工具,於是相關使用者通常只能通過學校圖書館並繳納一定費用後才能獲得此一查重服務。在此,知網是否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對於上述第一個環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已於2022年5月13日正式立案調查。對於上述第二個環節,則是有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郭兵於2021年12月通過浙江移動微法院起訴知網,指控其違反《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的規定,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22年3月21日正式受理此案。
由於上述兩案還在進行當中,社會各界也已經提出了相當多的討論,本文擬提出以下四個問題,以期集思廣益:
其一,舉證要求與責任配置問題。假定知網的相關市場的定義和範圍,是面向中國境內的在線論文數據庫服務市場(包括檢索、上傳與下載和其他的周邊服務,如“查重”功能等)。知網從一開始便是在行政特許的保護傘下形成獨特的市場壟斷地位,其在掌握與匯集絕大多數的信息方面都遙遙領先,諸如萬方、維普等與其有競爭關系的其他數據庫都難以望其項背(姑不論是否取得合法的著作權許可)。參酌擬議中的《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濫用規定》(草案)),知網所謂“借雞生蛋”的運營與盈利模式本身是否符合《濫用規定》(草案)的相關規定,尤其是其第22條?需要達到如何的舉證要求與標準?應由何方來承擔舉證責任?法院或執法機構是否可以迳行推定相關事項?
其二,促進競爭與利益平衡問題。鑒於在線論文數據庫服務市場寓含重要的公益色彩,一旦導入利益平衡要求,是否會與促進競爭產生競合;特別地,這是否會與“使用者付費”的基本原則沖突?亦即,如果真正貫徹《反壟斷法》的精神,同時鼓勵競爭與合法許可使用他人的著作權,是否將導致知網面臨拆解的結果,使得使用者至少在相關市場重新調整的期間內面臨相當的不便,無法從單一或主要來源獲取所需的檢索結果,顯著增加相關的檢索時間、費用等各項成本,降低檢索結果的質量?
其三,單方設限與濫用壟斷問題。《反壟斷法》是為了規制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而設,以間接保護消費者的福祉或經濟利益。知網從一開始就未將其論文查重系統或功能直接向個別的使用者(自然人)開放,僅此單一的舉措是否足以構成“濫用壟斷地位”?由於以往個人使用者依然可以通過單位或機構的賬戶獲得查重服務,其他的競爭者也提供了類似的功能,有無任何的實證調研顯示知網開放查重服務給個別使用者將導致促進競爭的結果,抑或強化知網的壟斷地位的結果?
其四,論理(合理)分析或當然違法問題。參考域外和國際間的立法與實踐,檢測被告是否從事了排斥性的行為時,一般采用所謂的“舉證轉換框架”(burden-shifting framework),或“合理分析”或“論理分析”(rule of reasons)法則,亦即主張權益受損的原告首先必須通過初步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證明被告的行為產生了反競爭效果,而後舉證責任便轉換至被告,被告可提出反證證明其行為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如果在此階段,反證無法成立,原告便獲得勝訴;如果反證能夠成立,舉證責任就再次轉移到原告,原告必須舉證被指控行為所造成的反競爭效果超過了其促進競爭所能帶來的利益。在知網案中,是否需要以此種更為細致的方式、更加複雜的經濟模型與分析來進行交叉比對,抑或簡單套用法律條款即可?何者更為妥當?
此外,即使直接套用現行《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或將來的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如前所述,由於知網過去從來沒有對個人直接開放使用其查重系統,這是否仍然構成“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查重功能是否算是“交易”?這裡還存在許多需要進一步商榷、研究之處。如果對於《反壟斷法》的上述條款采取廣義或擴張解釋,是否可能反而產生阻礙創新的後果,導致廠家為了避免法律風險而放棄對新功能、新服務的開發,削減消費者或社會大眾的福利?
結論
數據檢索已成為當今日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確保數據庫,尤其是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研究系統的功效性、正確性和完整性,也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公信建設工程。
伴隨其本身創立的特殊背景和長年以來收錄文獻的“擦邊球”手法,知網形同“空手奪刀”,以買空賣空、慷他人之慨的方式賺取高額的利潤,坐上了當前中文在線論文數據庫服務市場的龍頭位置。然而,不計其數的著作侵權糾紛,證明了這個看似龐大的數據庫實際上可能只是虛有其表的一座“紙牌屋”,欠缺最起碼的合法著作權基礎。此外,因牽扯論文檢索的重要社會公益,知網實際上織出了一張讓自己與法律都難過的網,其所引發的各種問題相互糾結、彼此沖突,無論如何處理,都勢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此類問題無法依靠法律完全妥善地解決,這再次凸顯了法律的局限性。
固然知網已經“從善如流”,和趙德馨教授達成了諒解與協議,把原先撤除的趙教授的文章悉數重新放回相關數據庫,但該事件引發的各項根本性問題卻仍懸而未決。例如,其他獲得勝訴卻依然遭到文章下架的原告又複如何?如果恢複其涉案文獻,固然滿足了社會公益的需求,但純粹就法論法,實際上造成了知網繼續侵權的結果,對此又應該如何處置?顯然,這些難題已無法純粹依靠法律解決。至於反壟斷的調查和訴訟,就更需要極度謹慎處理,尤其需要依靠詳盡可靠的實證調研與經濟分析。牽一發可動全身,知網案所牽涉的不僅是知網一家的問題,而是未來整個數據庫產業的發展。
歸根結底,知網案引發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各方協商以妥善處理,必須避免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將該事件導向零和博弈,避免任何一方“贏得戰役卻輸掉戰爭”的結果。對此,美國的“塔西尼案”無疑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負面教訓!
[28]例如,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與政策研究院楊勇認為,“若知網高價向高校銷售數據庫,通過“降評級”“下架論文”等措施“迫使”期刊授權,涉嫌違反該條第1項規定;知網拒絕向個人提供查重服務涉嫌違反第3項規定。然而,楊勇卻沒有展開其論證過程,頗為可惜。參見楊勇,淺析論文查重和下載服務的法律規制——從知網涉壟斷行為調查談起,《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2022年5月23日,載於《網輿勘策院》網站https://mp.weixin.qq.com/s/dHltoAKvRO_JN6o87Htz4g。
文章來源《中國知識產權》雜志第18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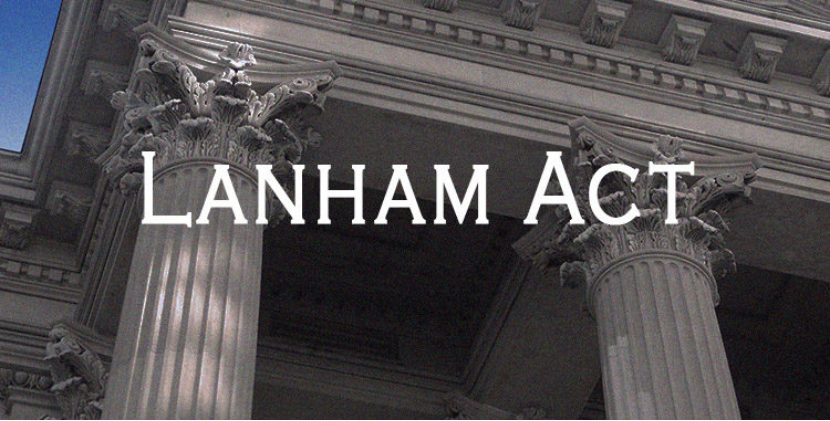


發表評論 取消回複